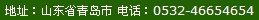|
巍巍天门,阅千年往事,只为顶天一立 从北方坐火车,一直南下,到大山突然从远处湛蓝的天空那边剪过来,然后一头撞进黑窟窿,一阵沉闷的轰鸣后,火车缓缓驶出峡谷,在秀丽的澧水平喘处,咣当一声停下来。这就到了张家界。 于是,你惊叹,阿麦嘎,张家界好美啊。 现代文明仿佛也是,强奸犯一样,从外面闯进来,在这古老的山体间,突然顶开一道口子,播下种子。 峡谷里至今仍残存着一股隐隐的萧杀之气。当年日本,就是麦克阿瑟用刺刀,将现代文明的种子强势输入的。 走下车,天光暗了许多,空气里漂忽着隐隐仙气;山青青的,水蓝蓝的,一缕清馨的气息,先是舔舔着鼻子,然后嗖的一下就蹿进身体里化开去。 哎呀妈,感觉真好,于是你会心地笑了。 清风吹拂,挂在大庸府城青铜墙上的那块招牌,像山姑娘变了少妇,独坐床头,怀念青涩年代一样。 之前的张家界,是那种懵懵懂懂还不知情为何物的处女。94年以后就不是了。 那以后,这个处女开始迎客了。一拨又一拨游人,迎来送往着就走上了旅游发展的历程,一路红尘滚滚。 最初那会儿还是大湘西,囊括大庸、吉首、怀化。行政划分也和现在不一样。 88年大庸立市后,旅游开发才起了张家界这个名字。原来的“大庸”渐渐从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模糊。 其实“大湘西”这个统称,还是很让人在乎的。早些年,去沿海打工,进厂主考官一听湘西的,眉头就锁起来。那时候正热播《乌龙山剿匪记》,在主考官眼里,湘西人个个都象“独眼龙”,惹不起。 这帮人平时窝里拱,对外却能迅速抱成团,这在沿海是出了名的。 那时候就觉得这就是“有种”,邪恶化了。这种情结,不是张家界人真很难体会。 未开化的农耕文明时代就是,好恶先放着,宗族利益至上,概念性抱团。 几十年过去,湘西人在沿海城市眼里,渐渐蜕变成了文明人,不再那么反感了,常常打工的老乡还能带回几个福建广东媳妇儿,这种文化与人情的交变,使我们大湘西又走近了文明一步。 只是骨子里我依然喜欢大湘西,和具有大湘西门头标志的这个庸城。中国人老喜欢改名字,地名、人名、山名都喜欢改来改去,这一招不知道是不是应验了中国人的精明与狡黠,和非典时“抢盐”,新冠时“抢连花”如出一辙。 也许是因为在不稳妥的环境里生活得太久,不得不投机取巧,不得不“盐荒子孙”。 记得刚从乡下进城来的时候,南门口还是小小的里弄,窄窄的石板路直抵澧水河岸;河水清清,乌篷船撑着高高的帘子,不时能听到里面渔姑荡出在河面上的歌声;黄昏,吃完晚饭的人们,从屋子里走出来,走到澧水河岸,孩子们挺挺肚皮,老人们打打太极,年轻的夫妻手拉着手走在河岸上,如同一起走过漫长的人生。 这就是我心中的庸城。 后来读石继丽的《天堂里没有陆弟》,忽然就觉得很怀念。怀念南门口的珰珰鼓鼓,怀念澧水河畔的吵吵闹闹,怀念宝塔岗鼓楼的钟声悠远。 那时候,生活气息很浓,离我这个从农村挤进来的土包子不远,庸城的人们都在地面上,踏踏实实的生活着。 那时候的庸城,古老而厚重。 更名以后,张家界这个名字,像翻新的涂料,将大庸两个字从传媒里抹去,在人们心里,传播得多了,也渐渐模糊了庸城原先的样子,庸城情感也开始粗糙起来。 起初我总改不过口,每次人家问起你是哪的呢?我就说我是大庸的。话一出口才知道又违和了。就像叫惯了二愣的,哪天看了本励志书忽然要你改口叫他志豪一样。其别扭其出离愤怒之后,呵呵一笑,那就这样吧。真是,大庸怎么着您了嘛。 不过那些年,紫舞街的马路倒是一沓比一沓宽起来,城管也一年比一年多;街道两边的楼,慢慢地高得你看不见顶。爬上党校,俯瞰这座城市,到处是挖机,铲车,和高高扬起的举升架。 举升架下那些蝼蚁般的人们,他们有的富了,有的穷了,富的因动迁而富,穷的也因动迁而穷。 旅游经济使张家界这块蛋糕越做越大,庸城原来的生活方式,慢慢地先是从三角坪退到大庸桥,又从大庸桥退到且住岗,不久且住岗也围起了高墙,高墙内,是那些不屑于青灯巷子、油炸麻花的共和国长子们,银行、烟草公司、中石化。 他们深居高墙,手握资源配置权,运筹如何把这块蛋糕做大,如何把这块蛋糕做精。那些长手长脚的可以零地价拿地,那些无权无势的被一步步逼退到郊外。 精品线、田罐罐、零地价、穿衣戴帽、哈利路亚等新名词充分搅拌,熬成一锅粥倾洒在“庸城”通往“张家界”的路上,正义、邪恶、纷争泥沙俱下。 横街竖港,到处写满“发展就是硬道理”的狠话,人们因城市动迁,在快速集聚的财富面前沉浮;随处的麻将桌,沿街的桑拿房,挤满了声色犬马的人们;有在动迁中钱已到手打算倒腾第二次的,有钱还没到手等着磨成钉子户的。总之,很少有人为这个城市寻求价值共识,也很少有人呵护那些不能失去的东西,人生苦短,都等着蛋糕做大,滚滚红尘一把。 城市的快速扩张,也催生了新的城市文化,人们很容易就忘记自己的来路,好像什么都可以推倒重来,“旧城”也好“旧事”也好,成了存放在一代人心里的隐痛。 如今,再有人提起文昌阁的米粉,南门口的篾货,后榕街的剃头匠,仿佛是上辈子的事。 那些灰头土脸的民工,抹完最后一道泥墙,就得离开了,血汗挥洒在了这座城市;那些推着板车卖菜,提着凳子擦鞋,背着背篓赶场的人们,开始象偷鸡贼一样,被以影响市容的名义驱赶;在这个日渐光鲜的城市,再也难找到他们的影子。 他们都去了哪里?都发财了么?都不用再那样了么? 今天就写到这里,象我这种野路子,就写个痛快,想到哪写到哪,什么你看现在的张家界变化多好呀之类,歌功颂德有端这碗饭的人在干,孔见杂记只是另辟一孔眼,个人感受,其实也会有"明白人",你太幼稚,我也接受。 另,所用图片源自网络,先谢谢了,如果图片发布者认为不妥,就联系我我立马删除。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:http://www.jishouzx.com/jssls/14150.html |
当前位置: 吉首市 >张家界杂记从大庸到张家界,我走瘸了一
时间:2024/4/18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彭武学致力六个奋力打造跑好全面建设现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